孙立尧:张栻以心论史说

提要:宋代是史论极其发达的时代,其间风格数变,而南宋史论的“理学化”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试以南宋理学家张栻的史论为例,论述南宋理学家“以心论史”的倾向及其价值。
关键词:史论;以心论史;仁;气象;诚
史论传统上是史学的一支,宋代则是史论最为发达的时代之一。但宋代史论表现出各种复杂的倾向,史学家或斥之为无益的“浮议”。如果将史论放在宋代宏大的学术背景之下来考察,则宋代史论的价值并不全由其史学意义来决定,如南宋众多史论的“理学意义”显然是超乎史学意义之上的。
理学在南宋臻于成熟,代表了有宋的核心学术。宋代理学家之史学,虽然于史事考证及著述历史的兴趣不大,但是其史观却表现出其纯粹性,其史论则更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张栻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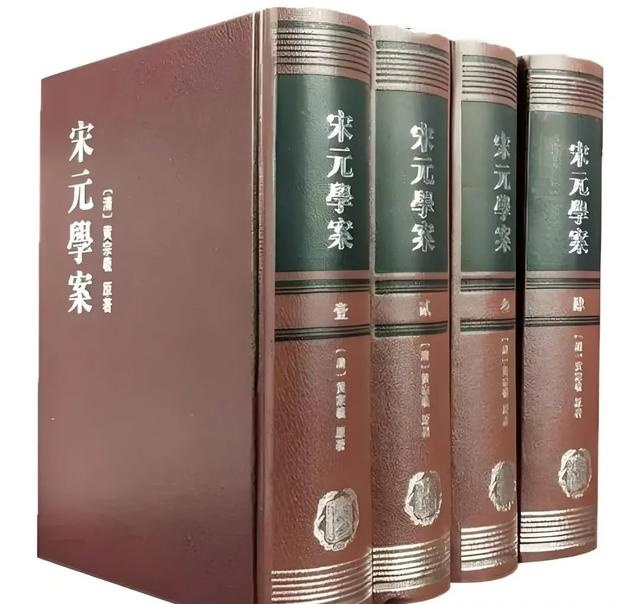
《宋元学案》现代版书影
一、南轩之学的核心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曾师事胡宏,而所造过于其师,故黄宗羲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1]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张栻天资甚高,朱熹尝称:“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2]全祖望也称:“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3]
宋代心学,虽可远溯自孟子,但北宋则以程颢为其发端,南宋有张九成、张栻等继之而起,而陆九渊总其成,故张栻的心学色彩是其学术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张栻之学,以“仁”为本,其《仁说》谓: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犹在《易》乾、坤四德而统言乾元、坤元也。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 [4]
案南轩此说,多本于程颢,程氏《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5]
“仁,人心也”,仁乃是本体,举此“仁”而仁、义、礼、智四者皆备,而亦为“人之性”。南轩所谓“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也就是程颢所说的“义、礼、知、信皆仁也”,“仁”实为南轩之学的本体。
为仁之法“莫要乎克己”,克己则无私,无私则与天地万物同体,故天理、人欲之分,义、利之辩,莫不由于克己之工夫,去一分己私(人欲),则得一分天理;而克己之法,在于“主一居敬”,是一种存养工夫,张氏曾作《主一箴》以阐发此修养方法:“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顺厥彝,则靡有忒。事物之感,纷纶朝夕。动而无节,生道或息。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须造次,是保是积。既久而精,乃会于极。勉哉勿倦,圣贤可则。”[6]为学之道莫过于此。也就是程颢所说的“以敬存之而已”。

国家图书馆藏《新刊南轩先生文集》明嘉靖元年(1522)刊本书影
惟其常行克己存养之功,则其气象乃大,史称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7]这也是张栻与同时儒者的不同之处,黄宗羲谓:“南轩早知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平日一段涵养工夫,至晚年而后悟也。”[8]张栻与吕祖谦的信中也说:“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存养处不深厚,故省察少力。”[9]其《南轩答问》同样阐明此点:
“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当审察其私,事事克之。[10]
人之天资万有不齐,皆待学而后能复其本然之善,学则是“克己”而已,由其工夫之差别,而有气象之不同。故张氏论人,亦常言及“天资”、“气象”,如谓张良“有儒者气象”,人之气象,必待学而后醇正,故张氏每于天资高者,而叹其不学。
由“克己”方能达到“无私”,才能够知“义”,因为所谓的“义”与“利”,也即是“公”与“私”之别而已,《宋史·道学传》述其“讲学之要”云:
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11]
与此相关联,“诚”也是其学术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惟无私者为能诚,亦惟诚者能感人,“君臣之际,须要自尽,积其诚意,庶几感通。其间丝毫未尽,恶能有动。” [12]又说:“念学力未到,诚意不能动人,只合退归,勉其在我。” [13]诚之既极,感通天地。《答俞秀才》中说:“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浑全一个诚意。至诚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 [14]其《孟子说》中论“格物”,也说:“所谓格者,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 [15]故“诚”亦是进学之道。
如此种种,在张氏论史之时,其核心要素皆有明白的体现,兹举例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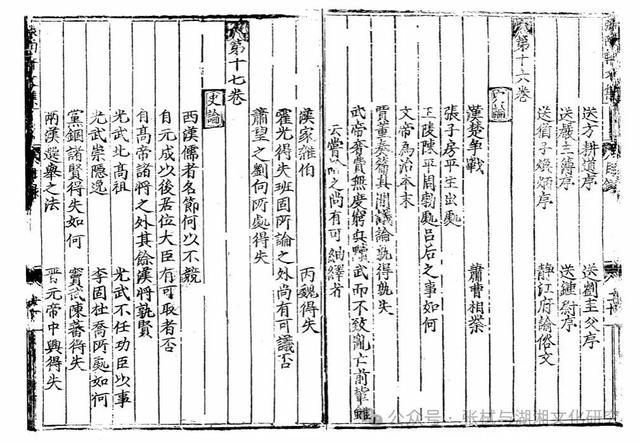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藏《新刊南轩先生文集》明嘉靖元年(1522)刊本书影
二、理欲与义利
《南轩集》中有史论两卷,颇能显示其一以贯之的学术,关于“义利”与“公私”之别,其分辨极为清楚。一己之私不能克,则不得为义。不义者,则入于利。义者天理,利者人欲。如其论《汉家杂伯》:
学者要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王伯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无所为而为之;伯者则莫非有为而然也。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载齐威、晋文之事,其间岂无可喜者,要莫非有所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术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谓汉家杂伯,固其所趋若此,然在汉家论之,则盖亦不易之论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后,反者数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趋也。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复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诚不孚也,则其伯固有自来。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资为近之,然其薰习操术,亦杂于黄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但其资美而术高耳,深考自可见。至于宣帝,则又伯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景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而以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窃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后世未尝真知王道,顾曰“儒生之说迂阔而难行”,盖亦未之思矣。[16]
这里所论的“天理”与“人欲”之别,是宋儒的核心议题,张氏持论与朱熹一致,王霸之辨即是义利之辨,即是天理与人欲之辨。故张氏《孟子讲义序》也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则一而已。”[17]
此处所谓“有所为”、“无所为”的分别,与文中所论的“无所为者天理,有所为者人欲”别无二致。这正是南轩之学的精要之一。执此以论史,则所论者在心不在迹,其要在于“心术之所存”而已,自春秋以至于汉代诸主,未有能够“无所为”者。
张氏从此点出发的史论甚多,如其《温峤得失》中论其绝裾之事:
温太真忠义慷慨,风节表著,足以为晋室名臣,古令所共推,不待详言。然吾独有所恨者,绝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穷达得失累其心,听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为也,于其身所处之义当然也。自后功名之裕兴而迁就趋避之说起,三纲始隳而不得其正,虽豪杰之士,为功名富贵所诱、失其性者多矣,可胜叹哉!太真少时尝以孝友笃至称,一旦奉刘琨之檄,将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于绝裾而行。噫,太真有母若此,身固不得已许琨矣,独不见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谓“方寸乱矣”,盖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独忍于此乎?若既以委质为人之臣,当危难而无可避可也,将命之举,岂无他人?太真念母,独不得辞乎?度其意,不过以江左将兴,奉檄劝进,徼幸投富贵之机、赴功名之会耳,而其所丧,不过甚乎?或曰:使太真不来江左,则宁复有后世之事业?太真固不得以两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业,皆非有所为而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怀希慕求必之心,则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异日之事,则凡背亲贼性命皆可以屑为,此三纲之所由坏,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齐固不受其国,夫子以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为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岂直太真之事业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晋室克复神州,一正天下,勋烈如此,浮云之过太虚耳,岂足以塞其天性之伤也?太真顺母之心而终其身,虽泯灭无闻于后,顾其所全者大,于身无愧,乌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谓太真称为功名之士则可,尚论古人,则可憾矣。[18]
张栻以为,温峤之绝裾,其心在于功名富贵,故为其一生之憾。此论于温峤的功业并未作过多渲染,反而认为即使温峤无此功名,若能顺母为孝,则其所得胜于此功名。况且此功名出于一己之私,是其心不正,更为南宋诸儒所不许。绝裾之事,前史未以为非,至张栻独能自这一小事中,推求其功名富贵之私心,谓其“徼幸投富贵之机、赴功名之会”,“怀希慕求必之心,则其私欲而已”,实际上是否定了其一生的功业,这正是张氏公私义利、有为无为之辨在史论中的直接反映,于此可见南宋诸儒的正本清源之功。
又如其论《晋元帝中兴得失》:
为国有大几,大几一失,则其弊随起而不可禁。所谓大几,三纲之所存是也。晋元帝初以怀帝之命,来临江左,当时之意,固以时事艰难,分建贤王以为屏翰,庶几增国家之势,折奸宄之心,缓急之际,实赖其纠率义旅,入卫王室,其责任盖不轻矣。而琅琊之入建业,考观其规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盖有自为封殖之意,而无慷慨谋国之诚。怀帝卒以蒙尘,迄不闻勤王之举,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诏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击楫渡江,聊复以兵应其请返从而制之,使不得有为,则其意不在中原也审矣。坐视神州板荡,戎马纵横,不以动其心,不过欲因时自利云耳。……使元帝痛怀、愍之难,笃君臣之义,念家国之雠,率江东英俊,鼓忠义之气,北向讨贼,义正理顺,安知中原无响应者?以区区一祖逖,倔强自立于群豪之间,犹几以自振,况肺腑之亲,总督之任,数路之势,何所不济哉?惟其不以至公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叹息也。其余得失,予不暇论,独推其本而言之。[19]
南轩之学,以克己为本,克己所以能大公,故其论晋元帝之中兴,仅就其心之公私立论,公私所以分义利,这也是为人立身之本,所以说“独推其本而言之”,独拈其大纲,至于其间细故得失,非复南轩所欲措意者。
又如其论《萧望之、刘向所处得失》,以为二人辅政之时,所处孤危,本当“艰深其虑,正固其守,诚意恳恻,以广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国势,谨其为,勿使有差,密其机,勿使或露,积之以久,上心开明,人才众多,群心归而理势顺,庶几有可为者。”然而二人最终之失,在于自行不正,用人不公,“不惟其贤,惟其附已”:
予观二子所执虽正,然恳诚之心不笃,势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义,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学之弊也。吁,可惜哉![20]
又《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中提及:“昔之儒者,学问素充,其施于用,随事著见,不蕲于立节,而其节不可夺,不蕲乎徇名,而其名随之,在己初无一毫加意也。”而汉儒“自叔孙通师弟子固皆以利禄为事,至于公孙丞相取相印封侯,学士皆群然歆慕之,其流如夏侯胜之刚果,犹有明经取青紫之言,况它人乎?盖其习俗胥靡之陋,一至于此,宜乎王莽篡窃之日,贡符献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洁者,班班仅有见于史也。”[21]原其要,皆出于一己利禄之心。又《光武不任功臣以事》中以为光武惩前汉功臣被诛之失,而“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终身”,汉高帝固然不是,而光武之不用寇、邓、贾复,则亦不得不为私:“盖用人之道,先有一说横于胸中,则为私意,非用人无方之义矣。”[22]又其论《王陵、陈平、周勃处吕后之事如何》认为“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而陈、周二人之所以如此者,也皆出于一己之私念:“予谓二子方对吕氏时,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汉之谋也。”[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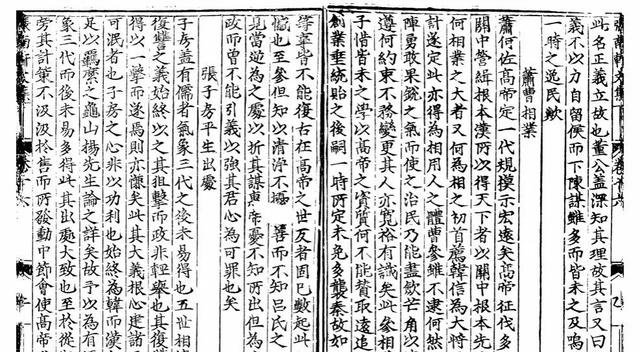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藏《新刊南轩先生文集》明嘉靖元年(1522)刊本书影
三、天资与学问
张氏论人,每言其“天资”、“气象”、“规模”,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常语。就张氏的学术而论,此三者皆有待于“学”的工夫而使其归于本初之“仁”,故张氏极重“学”,即克己存养的工夫。如其论《张子房平生出处》:
子房盖有儒者气象,三代之后,未易得也。五世相韩,笃《春秋》复雠之义,始终以之。其狙击秦政,非轻举也,其复雠之心,苟得以一击而遂焉,则亦慊矣。此其大义根心,建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终为韩,而汉之爵禄不足以羁縻之,龟山杨先生论之详矣。故予以为有儒者之气象,三代而后未易多得,此其出处大致也。至于从容高帝之旁,其计策不汲汲于售,而所发动中节会使高帝从之有不庸释者,盖子房非有求于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动无不得。此岂独可以知计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视隋何、郦食其、陆贾辈皆侮而忽之,至于如萧相国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顾也。独于子房盖敬而不敢慢,顺而不可强,则以子房所守在义,而不以利故尔。嗟乎!秦汉以来,士贱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骄之哉?虽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虚已以听信子房,盖亦可谓明也已矣!可谓明也已矣![24]
子房气象之所以大,乃在于其“所守在义,而不以利”,是“无功利之心”,即是公心,而非一己之私,故其“大义根心,建诸天地而不可泯”,“守义”亦即“克己”,故谓其“有儒者气象”。《霍光得失班固所论之外尙有可议否》中论霍光之得失,系其“天资”与“学”,惟其天资厚重,故能成其功;由其不学,故其不知义利之分,而为一己之利所毁:
霍光天资重厚,故可以当大事,而其所以失,则由于不学之故也。……孟子曰:“事亲若曾子可也。”而后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亲,适为人子之能尽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盖在其身所当为者,而何一毫有于己也?周公惟无一毫有于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业为无穷也。光之所建立想负于其身,横于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气焰不可掩,威势日以盛。权利之途,人争趋之,非惟家人子弟,门生故吏驯习骄纵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国、败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时用舍进退,例出于私意。……原其始,皆由于其心以宠利居成功,不知为人臣之分,故曰:不学之过也。虽然,后之儒生如班固辈,盖尝以不学病光矣,然使其当小利害,仅如毫发,鲜不丧其所守。望其如光凛然当大事,屹如山岳,其可得哉!然则光虽有不学之病,而其自得于天资者,盖亦有不可及。后之儒生虽自号为学者,讥议前人,而反无以自立,则亦何贵乎学哉?予谓人才如光辈,学者要当观其大节,先取其所长,而后议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则庶几为蓄德之要。不然,所论虽似高,亦为虚言而巳矣。[25]
如此之类,所论不少。南轩之学,贵能敛其习气,学养既深,故能浑厚而无英气发露。其与朱熹之书中屡言之,如:“来者多云会聚之间,酒酣气张,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时血气之习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习气难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觉乘快偏了。”[26]“年来务欲收敛,于本原处下功,觉得应事挡物时差贴贴地。但气习露见处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过。”[27]故其论史之际,也特重此点。如其《贾、董奏篇,其间议论孰得孰失》中评骘贾、董之气象不同,一出于天资之高明,一出于学问之淳厚,而董胜于贾,则为“知学”之功:
贾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则知学者也。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乎有激发暴露之气,其才则然也。天人之对,虽若缓而不切,然反复诵味,渊源纯粹,盖有余意,以其自学问涵养中来也。读其奏篇,则二子气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处语默,亦可验于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听仲舒之言,则天下蒙其福矣。孰谓缓而不切邪?[28]
执此为评骘标准,衡论历史人物处甚多。如《自高帝诸将之外其余汉将孰贤》以赵充国为汉将之最:“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予谓充国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定制度,为后世思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皆当在其下风耳。”[29]论《光武比高祖》:“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而至于光武之善守,则复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资极高,所不足者学耳。即位之后所以维持经理者,类皆疏略,雄杰之气不能自敛,卒至平城之辱。……嗟乎,以高祖之天资,使之知学之当务,则汤、武之圣,亦岂不可至哉?是尤可叹息也。”[30]又论《萧曹相业》:“曹参虽不逮何,然以摧锋陷阵、勇敢果锐之气,而使之治民,乃能尽敛芒角,以清净为道,遵何约束,不务变更,其人亦宽裕有识矣,此参相业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学,以高帝之资质,何不能赞取远追三代之法,创业垂统,贻之后嗣。一时所定,未免多袭秦故。”[31]又如论《文帝为治本末》:“其辞气温润不迫,其义诚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然而惜文帝无道学之臣,“以文帝天资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时,得道学之臣佐之,治功之起,岂不可追三代之余风?惜其大臣不过绛、灌、申屠嘉之徒,独有一贾谊,为当时英俊,而谊之身盖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见庸也。”[32]《党锢诸贤得失如何》则纯是论诸人之天资:
东京党锢诸君子,盖嘉其志气之美,而惜其所处之未尽。重其天资之高,而叹其于学有所未足也。……若诸君子之不为死生祸福易操,其间如李膺、杜密、陈蕃辈,卓然一时,其天资可谓刚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从事于圣门也,故所行虽正,立节虽严,未免发于意气之所动,而非循乎义理之安,出于恶其声之所感,而未尽夫恻隐之实。处之有未尽,固其宜也。岂非于学有不足欤?使其在圣门,则当入于仲由之科,圣人抑扬矫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为陈太邱之事为得其中,以予观之,太邱在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盖天资又加美焉耳。而其所处张让之事,亦非中节,在当时,隐迹自晦,岂无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为矫失之过,以此免祸,君子亦不贵也。不然,则郭有道乎?识高而量洪,才优而虑远,足为当时人物之领袖,然收敛之功犹未之尽,要亦于学有欠也。不然,则黄叔度乎?言论风旨,虽不尽见,然其气象温厚,圭角浑然,见之者有所感于心,其为最高乎?使在圣门作成之,当居颜氏之科矣。[33]
由此可见,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虽然可以由其天资而有所得,但若辅以后天培养之功,则所造当更进一步,这也是南宋诸儒发明学问的得力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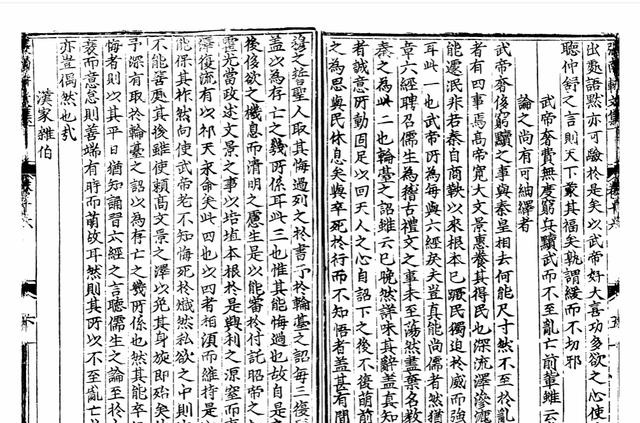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藏《新刊南轩先生文集》明嘉靖元年刊本书影
四、论“诚”
张氏史论中也极重视“诚”的重要性,学问事业的真正成就,未有不来源于“诚”者。如《武帝奢费无度,穷兵黩武,而不至乱亡。前辈虽云尝论之,尚有可紬绎者》:
武帝奢侈穷黩之事,与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于乱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宽大,文、景惠养,其得民也深,流泽渗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来,根本已蹶,民独迫于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为,每与六经戾,夫岂真能尚儒者,然犹表章六经,聘召儒生,为稽古礼文之事,未至荡然尽弃名教,如秦之为,此二也。轮台之诏,虽云已晚,然详味其辞,盖真知悔者,诚意所动,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诏下之后,不复萌前日之为,思与民休息矣。与卒死于行,而不知悟者,盖甚有间。秦穆之誓,圣人取其悔过,列之于《书》,予于轮台之诏,每三复焉,盖以为存亡之几所系耳,此三也。惟其能悔过也,故自是之后,侈欲之机息而清明之虑生,是以能审于付托。昭帝之初,霍光当政,述文、景之事,以培埴本根,于是兴利之源窒,而惠泽复流,有以祁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须而维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于炽然私欲之中,则决不能善处其后,虽使赖高、文、景之泽,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于轮台之诏,以为存亡之几所系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则以其平日犹知诵习六经之言,听儒生之论,至于力衰而意怠,则善端有时而萌故耳。然则其所以不至乱亡者,亦岂偶然也哉![34]
“诚意所动,固足以回天人之心”,此亦是张氏一贯之说,如前文所引其论周公之事亦然。而在其论《汉楚争战》时也论及汉高祖为义帝缟素,声项羽之罪而讨之,“使斯时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会,率诸侯穷羽所至而诛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诚意不笃,不能遂收汤、武之功。”[35]又其论《谢安淝水之功》,“以予观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义纯固,负荷国事,直欲与晋室同存亡,故能运用英豪,克成勋业,诚与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诚与才合,不足以济。”[36]
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与其学术密切相关的。总之,这几点在张氏之学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在其发为史论之际,自然也就处处关联到其学术上来。论史意在事先,是南宋诸儒的通则,张氏自不例外。

南轩书院前纳湖小景 吴明元 摄
结 论
南宋史论与北宋史论大不相同,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既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化相关,也与学术本身的演变有关。“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37]若就学术本身而论,北宋之学与南宋之学的不同,用一句简明的话来概括,即北宋学者偏重于在“修齐治平”上下功夫,而南宋学者则进一步将着力点放在“格致诚正”上。易言之,北宋之学“致广大”,而南宋之学“尽精微”。
南北宋之交的学术转型,刘子健称之为“文化内向”,引起这一变化的因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动荡,金人的入侵,道德的崩溃,一切都导致了北宋悲剧性的灭亡。“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他们熟识或曾闻其名的众多士大夫的无耻行径。”[38]北宋以来士大夫所热心的制度建设不再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部分,他们转而相信重建道德是惟一的出路,从而成为道德保守主义者(moralistic conservatives)。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个人修养,因此南宋时期进一步向个人道德方面转化:
总得来说,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向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的或政治秩序构架当中的道德观念。[39][6](P141)
因此,从“修齐治平”到“格致诚正”的转变也成为一种必然。这种转变延伸到各领域。就史论而言,理学家的史论之中尤其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如胡寅、张栻、朱熹、吕祖谦、袁燮、钱时等,多有体现。历史人物的政治功业不再是史论家兴趣的焦点,他们转而探讨历史人物的心术,如“正心、诚意”等自我修养在历史中的表现,并以此来断其优劣或吸取历史经验。南宋儒者“转向内在”在史论领域中的具体呈现,其所论虽似与历史脱节,却正是理学家一种独特的历史探讨方式。
张栻则正是这种论史方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清人陈钟祥所说认为张栻史论综合“班、马之长”,[40]其实并未切中肯綮,只是从文章角度而言的泛泛之论。事实上,史论中多论人物之行事动机,这是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特色。张栻之学更近于心学,故论史也多就其心地而言。以心论史,乃是究极立论,故也超越历史本身,从而导致与史学的分离。然而圣贤之学,莫不于起心动念处推究,故张栻的史论,实是与其学术相结合的最好典范。因而,张氏以其学而论史,论断简切纯粹,足以为南宋理学家史论的代表。
